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英語:,常缩写为CABG)或心臟繞道手術,俗称冠脉搭桥或搭桥,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是一项缓解心绞痛和减少冠心病死亡风险的手术。搭桥所用的动脉或静脉均来自患者自身(乳内动脉、桡动脉、胃网膜右动脉、大隐静脉)。将血管桥接于冠状动脉,以绕过冠脉粥样硬化狭窄部,从而提高冠脉灌注,增加心肌氧供。这项手术通常在心脏停搏下进行,需使用体外循环支持; 而搭桥手术也可在跳动的心脏上进行,所谓的“非体外循环(off-pump)”手术。
| 冠状动脉搭桥术 | |
|---|---|
 冠脉搭桥术前期,静脉从腿上截取(图片左边)及建立体外循环(留置主动脉套管)(图片下方)。灌注师及体外循环机器位于右上方。患者的头部(被挡住)位于下方 | |
| ICD-10-PCS | 021209W |
| ICD-9-CM | 36.1 |
| MeSH | D0010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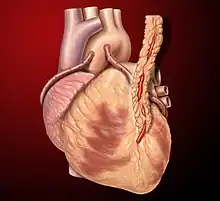
历史
第一例冠脉搭桥术于1960年5月2日,在美国Albert Einstein医学院-Bronx市立中心医院施行的。由Robert Goetz医生和胸外科医生Micheal Rohman领队,以及Jordan Haller和Ronald Dee医生为助手的小组完成。[1][2] 这个技术是将血管通过环形嵌入的金属环相连。以乳内动脉用作血管桥,吻合于右冠状动脉。真正使用Rosenbach环的吻合术进行了15秒,没有依靠体外循环。使用乳内动脉的不足在于,9个月后的尸检发现吻合口仍通畅,但是粥样硬化斑块阻塞了乳内动脉的起始端。
俄国心外科医生Vasilii Kolesov,被证实是第一个成功实施乳内动脉-冠状动脉吻合术(1964年)。[3][4]
然而,Goetz的技术被其他人所引用,包括第一个成功实施人类冠脉搭桥术[5][6][7][8][9][10][11]的Kolesov。[12]Goetz的手术病例经常被人忽视,这是由于缺少充足的报道,以及对于创造的吻合方式的错误理解,使一些疑惑持续了40多年。血管的吻合是内膜-内膜式的,通过一个特殊设计的金属环,血管被连接在一起。而Kolesov是通过标准的缝合技术,于1964年成功完成了第一例冠脉搭桥,在之后的五年中,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完成了33例相关的缝合及机械吻合。[13][14]
阿根廷外科医生勒內·法瓦洛羅,对于搭桥血管的选择上有了新的突破(1967年5月在克里夫兰诊所)。[4][15]他的新技术是使用自体的大隐静脉,来取代右冠状动脉狭窄段。之后他又成功使用大隐静脉作为血管通路,而这项技术成为了当今我们所知的典型旁路移植术; 在美国,大隐静脉是经内镜所获取的,通过一种“内窥镜取血管术(EVH)”的技术。不久Dudley Johnson医生扩展了旁路移植技术,涵盖了左冠状动脉系统。[4]在1968年Charles Bailey、Teruo Hirose和George Green医生在搭桥术中,用乳内动脉取代大隐静脉。[4]
术语
术语上有许多变化,比如“动脉”、“旁路”或“移植”字眼被省去。这类手术所使用最常见的缩写是CABG(发音同cabbage),[16] 复数形式是CABGs(发音同cabbages)。最近,术语主动脉冠状动脉搭桥(ACB)的使用变得普遍。CAGS(冠状动脉搭桥术)不可与CAG(冠状动脉造影)混淆。
动脉硬化是常见的动脉病变,特点是管壁增厚,失去弹性,管壁钙化,由此造成血液供应减少。
动脉粥样硬化特点是大、中动脉内层,有淡黄色胆固醇斑块、血脂以及细胞碎片沉积。
搭桥的数量
一些术语如单支搭桥、双支搭桥、三支搭桥、四支搭桥、五支搭桥是指搭桥术中涉及的冠状动脉数量。也就是说双支搭桥手术意味着两条冠状动脉被行搭桥(如左前降支和右冠状动脉);三支搭桥意味着有三条冠状动脉被行搭桥(如左前降支、右冠状动脉、左回旋支);四支搭桥意味着有四条冠状动脉被行搭桥(如左前降支、右冠状动脉、左回旋支,左前降支第一对角支);五支搭桥意味有五条。搭桥术涉及四条冠状动脉以上并不常见。
搭桥数量越多并不等同病人更危重,同样搭桥数量越少也不等同病人更健康。[17]一个有大量冠脉病变的患者由于缺乏合适的“靶血管”,也许将接受相对少的搭桥。一条冠状动脉如果太细(<1mm或<1.5mm 取决于外科医生)、严重钙化(意味着冠状动脉没有节段免于冠脉疾病的侵犯)或心肌桥(冠状动脉行走于心肌间而非心脏表面),也许就并不适合行搭桥术。同样一位病人若仅左主干狭窄,则只需要两次搭桥(左前降支和左回旋支)。然而,左主干病变是心脏病导致死亡的最大风险。
外科医生术前会评估冠脉造影结果,以确定冠脉病变的部位。外科医生会术前会估算搭桥的数量,但最终的定夺是在手术室,经心脏检查后决定的。
冠脉搭桥的指征
对于冠状动脉疾病有一些替代疗法。它们包括:
- 药物治疗(抗心绞痛药物附加他汀类药物,降压药,戒烟以及糖尿病者的血糖严格控制)
- 支架介入治疗(PCI)
Hi 在症状(如心绞痛,呼吸困难,疲乏)缓解方面,介入治疗和冠脉搭桥都要比药物治疗更为有效。[18]对于一些多支冠脉病变的患者而言,冠脉搭桥的疗效要优于介入治疗。[19][20]
SoS(手术还是支架)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该试验用于比较冠脉搭桥和裸金属支架的介入治疗。SoS研究证明在多支冠脉病变的治疗中,冠脉搭桥要优于介入治疗。[19]
SYNTAX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对象为1800名多支冠脉病变的患者,将冠脉搭桥和药物洗脱支架(DES)的介入治疗做比较。研究发现药物洗脱支架组在过去12个月中,心脏或脑血管的主要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出(冠脉搭桥12.4% VS 药物洗脱支架17.8% P=0.002)。[20] 这主要由于在介入治疗组中,需要更多的再次血管重建,但两组试验在术后再梗阻或存活上没有差别。冠脉搭桥组的中风发病率更高。
FREEDOM(患者合并糖尿病的远期血管重建评估──多支血管病变的最佳治疗)研究将在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中比较冠脉搭桥和药物洗脱支架的疗效。试验中,为非随机筛选的病人所做的记录,将提供更多关于血管重建结果的强大数据,以用做随机分析。[21]
一项研究比较了在纽约州,所有通过冠脉搭桥或介入治疗的病人的疗效,结果表明在多支冠脉病变中,冠脉搭桥胜于药物洗脱支架的介入治疗。通过冠脉搭桥治疗的病人,在死亡率或心肌梗死率上比使用支架的更低。通过冠脉搭桥的患者,其再次血管重建率也更低。[22] 纽约州登记处包括所有因为冠状动脉疾病而经历血管重建的病人,但这并不是随机试验,因此除反应冠脉血管重建的影响因素外,还可能反应了其他因素。
2004年ACC(美国心脏病学院)/AHA(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中说明了冠脉搭桥在以下情况中作为首选治疗:[23]
- 左主冠状动脉病变
- 所有三支冠状动脉病变(左前降支、右冠状动脉和左回旋支)
- 不适合通过介入治疗的弥漫性疾病
2005年ACC(美国心脏病学院)/AHA(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进一步指出:在合并其他高风险疾病比如严重心功能不全(如低射血分数)或糖尿病的患者中,冠脉搭桥是首选治疗。[23]
预后
冠脉搭桥的预后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成功的搭桥通常能维持10–15年。通常冠脉搭桥提高了高危病人(心肌缺血而导致心绞痛)的生存机率,但是在统计学上,关于冠脉搭桥和药物治疗的生存率,两者的差异在五年后递减。冠脉搭桥的年龄对于预后很重要,年轻且没有合并症的患者有更高长寿的机率。年老的病人通常会经受进一步的冠脉阻塞。
争议
对于冠脉搭桥术在拯救心脏病(通过立即缓解梗阻)的价值,在多项研究中被明确认可,但是在稳定性心绞痛中,研究无法明确搭桥术相比药物治疗的优势。 冠脉搭桥可暂时性地缓解胸痛,但是不能延长寿命。绝大部分心脏病的源头并非冠脉阻塞狭窄,而是吸烟、高胆固醇、高血脂症和高血压等。[24]
心智功能丧失是冠脉搭桥常见的并发症,影响到对手术成本-效益的考虑。一份出版的调查通过对冠脉搭桥术后MRI图像的研究表明,51%的术后病人有明显脑部损伤。[25]
一些因素或许促成了认知功能下降。体外循环系统和手术本身会释放各种碎片,包括少量的血细胞及斑块。例如,当外科医生夹钳以及连接主动脉至套管时,产生的血栓会阻断血流从而引起微小中风。其他与心脏手术相关的心理机能损伤因素包括低氧、高或低体温、异常血压、不规则心率以及术后发热。
一个能避免患者处于心脏病高危等级,且更安全、更永久、更成功的方法是去锻炼、戒烟、服药控制血压以及降低胆固醇以防止血液凝集。[24] 从更长远来看,行为以及药物治疗可能是,避免血管因素引起心智功能丧失的唯一途径。[26]
简要手术过程
- 患者进入手术室,移上手术台
- 麻醉医师给患者置入外周静脉导管,置入动脉导管连续监测血压。注射诱导麻醉剂(通常是丙泊酚)使患者处于无意识状态,数分钟后注射镇痛剂(通常是芬太尼),注射肌肉鬆弛劑使患者肌肉松弛。
- 气管插管,由麻醉医师或者助手(如呼吸治疗师或护士麻醉师)监护,以及呼吸机启动。镇静、镇痛药物的缓慢持续注射以维持全身麻醉,持续输注或间断给予肌松药物。
- 由麻醉医生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必要时置入漂浮导管监测肺动脉压、心输出量。
- 外科医生经胸骨中线切开打开胸腔,检查心脏
- 截取搭桥用的血管──一般选取的是乳内动脉,桡动脉和大隐静脉。当选取完成后,给予病人肝素以防止血液凝固
- 如果是“非体外循环”手术,外科医生放置装备以稳定心脏
- 如果是“体外循环”手术,外科医生先在心脏处缝合套管,指示灌注师开始体外循环。一旦体外循环建立,外科医生于主动脉处放置主动脉钳,并指示灌注师向心脏注入停搏液(通常是特殊的钾混合液,冷的)以停止心跳,减缓新陈代谢。通常患者体外机械循环的血液被冷却至大约84°F (29°C)
- 血管桥的一端缝合至冠脉阻塞处的远端,另一端连接于主动脉
- 心脏恢复搏动;或在“非体外循环”手术中,稳定心脏的装备移除。在某些情况下,在主动脉的一部分由c形钳钳住后,使心脏恢复搏动,钳住部位在心脏搏动的情况下用于缝合血管桥
- 鱼精蛋白用来逆转肝素的作用
- 连接胸骨,缝合关闭胸腔
- 患者被移至重症监护病房恢复。在重症监护病房苏醒和稳定后(大约1天),患者转入心外科病房直至出院(大约4天)
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术
一种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术的替代疗法近年开始发展。非体外循环的冠脉搭桥术(OPCAB)是一项不借助于体外循环,而进行的冠脉搭桥术。[27]非体外循环的冠脉搭桥术(OPCAB)的进一步改进即为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MIDCAB),手术是通过一个5至10厘米的切口进行。[28]
血管桥的选取
血管的选择很大取决于特定的外科医生和医疗机构。通常,左侧胸廓内动脉(先前提及的左乳内动脉)移接至左前降支,另一些动静脉被联合使用于其他冠脉搭桥。右侧胸廓内动脉,腿部的大隐静脉和前臂的桡动脉也常被使用。在美国,这些血管通常是经内镜获取的,通过一种“内窥镜取血管术(EVH)”的技术。胃部的胃网膜右动脉不常使用,是由于其从腹腔移取的困难性。
血管桥的通畅
冠脉搭桥术后的几个月至几年,血管桥会病变且可能阻塞。通畅是个用来形容血管桥保持开放可能的术语。如果血管桥内有血流且无显著(>70%直径)的狭窄,那血管桥是被认作通畅的。
血管桥的通畅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血管桥的类型、大小选取(胸廓内动脉,桡动脉,或者大隐静脉),或血管桥相接的冠状动脉,当然外科医生手术技能也是。动脉桥(如左侧胸廓内动脉、桡动脉)对于粗暴处理的敏感度远高于大隐静脉,且不适当的处理会导致血管痉挛。
一般最佳的通畅率是由原位的左侧胸廓内动脉(近端保留与锁骨下动脉相连)的远端与冠状动脉相吻合(通常为左前降支或对角支)。稍低的通畅率可见于桡动脉和“游离”的胸廓内动脉(胸廓内动脉的近端与锁骨下动脉断离后再与升主动脉吻合)。大隐静脉的通畅率最差,但当患者有不同的冠状动脉需要搭桥时,大隐静脉可分为多个节段以供搭桥。
所使用的静脉不是去除了静脉瓣就是倒置连接,这样静脉瓣不会阻塞血管桥的血流。左侧胸廓内动脉桥比静脉桥维持时间长,既是由于动脉比静脉结实,还因为左侧胸廓内动脉只需一端连接至冠脉,而静脉需要两端分别连接至主动脉和冠脉。左侧胸廓内动脉通常用于吻合至左前降支,这是因为其长期通畅度远高于大隐静脉。[29][30]
胸骨的注意事项
患者在接受冠脉搭桥后的8到12周内需避免做某些事情,以减少切口裂开的风险。这些措施称为胸骨的注意事项。首先,患者需要避免过度使用手臂,比如将自己推离座椅或在坐下前拖座位。为了避免这个,患者被鼓励在站起之前,先在座位上摇摆几次以增加冲力。其次,患者应该避免提任何超过5-10磅的东西。一加仑牛奶大概重8.5磅,这是一个很好的重量限制参考点。最后,患者应该避免将手举过头做事,比如从衣橱的顶架上取毛衣或者从橱柜里取碟子或杯子。
并发症
经冠脉搭桥的患者,术后除了会有和其他手术一样的并发症外,外加一些冠脉搭桥中更常见或特有的风险。
与冠脉搭桥相关
- 灌注后综合症,是与体外循环相关的一过性神经认知功能障碍。一些研究表明,最初的发生率在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中下降,但术后三个月后就与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没有差别。随着时间推移,无论什么治疗(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术,传统冠脉搭桥术或药物治疗),神经认知功能降低皆已体现在冠脉疾病的患者身上。然而2009年的研究表明,长期(超过5年)的认知功能下降不是由于冠脉搭桥引起的,而是血管病变的后果。[31]
- 胸骨不愈合:胸廓内动脉的截取使胸骨缺少血供而增加风险
- 由于栓塞,低灌注或者搭桥失败导致心肌梗死
- 晚期血管桥狭窄,大多发生于大隐静脉桥,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经常性心绞痛或心肌梗死
- 由于栓塞或低灌注导致的急性肾衰
- 中风,由于栓塞或低灌注
- 血管麻痹综合征,由于体外循环或低灌注
- 搭桥维持8-15年后,需要替换
- 气胸:空气聚集在肺周围且压迫肺
- 血胸:血液聚集在肺周空隙
- 心包填塞:血液聚集在心脏周围且压迫心脏,从而引起体循环及大脑灌注低。胸腔引流管置于心肺周围可以避免此发生。如果胸腔引流管在术后早期阻塞,而出血仍在继续,那么这会导致心包填塞、气胸或血胸。
- 胸腔积液:液体在肺周围渗出。这会应引起低氧血症且恢复缓慢。
与心脏手术相关
术后房颤:心脏手术后有时会出现心律失常
与普通手术相关
- 切口感染或败血症
- 深静脉血栓
- 麻醉并发症如恶性高热
- 瘢痕疙瘩
- 切开口慢性疼痛
- 应激相关的慢性疾病
- 死亡
参见
- 血管成形术
- 心胸外科
- 後心肌梗塞症候群
- “杂交”手术(冠脉搭桥合并冠脉内支架)
- 完全内镜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 胸腔引流管
参考
- Dee, R. . Tex Heart Inst J (Houston: Texas Heart Institute). 2003, 30 (1): 90. PMC 152850
 . PMID 12638685.
. PMID 12638685. - Haller, JD; Olearchyk, AS. . Tex Heart Inst J (Houston: Texas Heart Institute). 2002, 29 (4): 342–4. PMC 140304
 . PMID 12484626.
. PMID 12484626. - Kolessov, VI. .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October 1967, 54 (4): 535–44. PMID 6051440.
- Mehta, NJ; Khan, IA. . Tex Heart Inst J. 2002, 29 (3): 164–71. PMC 124754
 . PMID 12224718.
. PMID 12224718. - Olearchyk, AS. . J Ukr Med Assoc North Am. 1988, 1 (117): 3–34.
- Olearchyk, AS; Olearchyk, RM. . Ann Thorac Surg. January 1999, 67 (1): 273–6. PMID 10086577. doi:10.1016/S0003-4975(98)01225-9.
- Glenn, WW. . Circulation. April 1972, 45 (4): 869–77. PMID 5016019.
- Ochsner JL, Mills NL. . Philadelphia: Lea & Febiger. 1978.
- Cushing, WJ; Magovern, GJ; Olearchyk, AS. .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November 1986, 92 (5): 963–4. PMID 3773554.
- Konstantinov, IE. . Ann Thorac Surg. June 2000, 69 (6): 1966–72. PMID 10892969. doi:10.1016/S0003-4975(00)01264-9.
- Konstantinov IE. . Einstein Q J Biol Med. 2000, 18: 73–8.
- Kolesov, VI; Potashov, LV. . Eksp Khir Anesteziol. 1965, 10 (2): 3–8. PMID 5851057 (俄语).
- Kolesov, VI; Kolesov, EV. .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February 1991, 101 (2): 360–1. PMID 1992247.
- Haller, JD; Olearchyk, AS. . Tex Heart Inst J. 2002, 29 (4): 342–4. PMC 140304
 . PMID 12484626.
. PMID 12484626. Reference 4
- Favaloro, RG; Effler, DB; Cheanvechai, C; Quint, RA; Sones Jr, FM. . Am J Cardiol. November 1971, 28 (5): 598–607. PMID 5116978. doi:10.1016/0002-9149(71)90104-4.
- .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March 26, 2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4-20).
- Ohki, S; Kaneko T; Satoh Y; et al. . Kyobu geka.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thoracic surgery. 2002, 55 (10): 829–33; discussion 833–6. PMID 12233100 (日语).
- Rihal C, Raco D, Gersh B, Yusuf S. . Circulation. 2003, 108 (20): 2439–45 [2011-11-16]. PMID 14623791. doi:10.1161/01.CIR.0000094405.21583.7C.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3-21).
- SoS Investigators. . Lancet. September 28, 2002, 360 (9338): 965–70. PMID 12383664. doi:10.1016/S0140-6736(02)11078-6.
- Serruys, P.W.; Morice M.-C.; Kappetein A.P.; et al. . N Engl J Med. March 5, 2009, 360 (10): 961–72. PMID 19228612. doi:10.1056/NEJMoa0804626.
- Desai ND. . Ann Thorac Surg. January 2008, 85 (1): 25–7. PMID 18154771. doi:10.1016/j.athoracsur.2007.08.063.
- Hannan, EL; Wu C; Walford G; et al. . N. Engl. J. Med. January 24, 2008, 358 (4): 331–41. PMID 18216353. doi:10.1056/NEJMoa071804.
- Eagle, KA; Guyton RA; Davidoff R; et al. . Circulation. October 5, 2004, 110 (14): e340–437. PMID 15466654.
- Kolata, Gina. "New Heart Studies Question the Value Of Opening Arteri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4. Retrieved January 14, 2011.
- Knipp SC, Matatko N, Wilhelm H, Schlamann M, Thielmann M, Lösch C, Diener HC, Jakob H. . Ann Thorac Surg. Mar 2008, 85 (3): 872–9. PMID 18291160. doi:10.1016/j.athoracsur.2007.10.083.
- Harmon, Katherine "Heart-Lung Machine May Not Be the Culprit in Post-Op "Pump Head" Syndrome"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6, 200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Sabik, Joseph. . Clevelandclinic.com. 2010 [February 28, 2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5).
- Sabik, Joseph. . Clevelandclinic.com. 2010 [February 28, 2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3).
- Kitamura, S; Kawachi K; Kawata T; et al. . Nippon Geka Gakkai Zasshi. March 1996, 97 (3): 202–9. PMID 8649330 (日语).
- Arima, M; Kanoh T; Suzuki T; et al. . Circ J. August 2005, 69 (8): 896–902 [2011年11月16日]. PMID 16041156. doi:10.1253/circj.69.89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6年3月18日).
- Harmon, Katherine. . ScientificAmerican.com. August 6, 2009 [February 2, 2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09).
外部链接
- A BBC film showing a patient undergoing a double bypass oper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Ischemic Heart Disease section in Cardiac Surgey in the Adult
-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at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s Cardiac and Vascular Institute
Template:Cardiac surg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