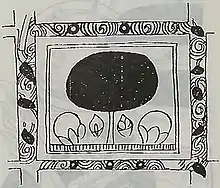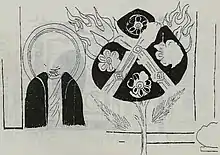吐峪沟石窟
吐峪沟石窟(英文:The Tuyoq Buddhist Grottoes)是新疆东部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群[1]。


| 吐峪沟石窟 | |
|---|---|
 吐峪沟石窟悬崖(Gregor Kneussel摄于2008) | |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 |
| 所在 | 吐鲁番市鄯善县 |
| 分类 | 石窟寺及石刻 |
| 时代 | 南北朝至唐 |
| 编号 | Ⅳ-63 |
| 登录 | 2006年5月25日 |
地理环境信息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西南距高昌故城10余公里。这里地处火焰山山脉 , 向南为洋海坎古墓 , 向北则为苏贝希古墓, 为连通火焰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2] 。追溯到5世纪,吐峪沟石窟的环境比现在更为温暖和湿润,所以在当时,吐峪沟是一处温暖潮湿的绿洲[3]。
主要遗迹
现有90余个洞窟,其中有编号46窟,按石窟窟形来分分为方型窟、中心柱窟和纵券顶窟;按类型来分分为支提窟、毗诃罗窟和讲经窟 [4]。
沟东区北部上层石窟群
沟东区北部上层石窟群位于沟东最北端。清理发掘的洞窟共计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其他配套生活设施等 [1]。并发现了吐峪沟石窟一些较为重要的遗迹现象包括部分重要石窟 、封闭石窟, 还有窟前建筑遗迹、门道、台阶, 以及各种改建、扩建 、重修现象[2]。
沟东区北部下层遗址群
发现1座塔庙窟,1座佛殿窟,窟前平台和寺院北侧墙垣遗迹。寺院北侧墙垣以外为淤泥堆积层,该区域与早期冲沟相连,用于寺院排洪[5]。
沟东区南部地面佛寺
回鹘地面佛寺位于沟东区南部,处于山间豁口斜坡上,面西背东,西面正对沟西的霍加姆麻扎。已揭露的部分包括一处佛堂和一组生活设施[1]。
沟西区中区石窟群
西岸中区窟群上下共分为5层,左右依据功用和布局可分为3个部分,规模十分宏大壮观。中区北段由两个中心柱式洞窟、一组禅窟和相关窟前遗迹( 佛塔、僧房等) 构成。两个中心柱式洞窟正面均残存像台,并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壁画和纸质文书[6]。
沟西区北部石窟群
沟西区北部石窟群为上下 4至5层的结构。由于山体崩坏,遗迹损毁较严重。最高一层仅在最西面残存一僧房窟,其余部分完全崩毁。第 2层的遗迹也几乎破坏殆尽,仅余最东侧的中心柱窟。第3层尚有部分残存。只有第4层位置靠下,因而保存遗迹相对较多,现已揭露面积约600平方 米。由于气候 原 因,下层的遗迹尚未完全揭露。已发现的遗迹有中心柱窟、禅窟和僧房窟[1]。
近期主要出土文物
历史
吐峪沟石窟兴建于公元443至460年之间,北凉在这段时期统治着高昌,北凉的统治对高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史》记载,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北凉灭亡后,到麴氏高昌时,皇室对佛教的重视只增不减。据《西州图经》记载,在唐朝时吐峪沟石窟被称为丁谷窟[18],佛窟规模不减,并有修缮。高昌回鹘期间,石窟被修缮[4]。数百年间,吐峪沟石窟荣登东疆第一宝窟之位。至公元15世纪时伊斯兰的到来,吐峪沟石窟遭才被废弃[19]。
近代考古及现状
19世纪中20世纪初,俄日英德等国探险队先后深入吐鲁番等地,窃取了大量文物包括壁畫、 雕刻、泥塑和各種古代語言寫的手稿 [20]。 其中:
- 1877年,俄国植物学家 A. Regel成为第一个到达此地进行调查的西方学者。而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克莱门兹等俄国探险家、东方学者分别于1893年、1897年和1912年来到此地并带走了很多壁画及佛教文献并先后出版《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1898年克莱门兹在吐鲁番的考察》等考察结果。其出土的文物现藏于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东方部中国馆[21]。
- 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于1904年,在此地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壁画回国后出版发行了《第一次普魯士皇家( 第二次德國 ) 吐魯番考察隊在中国突厥斯坦記行和考察結果簡報》。1906年至1907年,同样是德国学者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对吐峪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后出版有《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等考察结果。文物首先被运回国内藏于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藏品转移出柏林,其中部分藏品被苏军带走现藏于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剩余由战后运回民俗博物馆,由印度艺术部(今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管理)[22]。
- 1903年,由大谷光瑞作为领队,由橘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组成的日本考察团对此地进行了4此考察出土并带走了当时出土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经典抄本。其中部分藏品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3]以及日本东京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24]。
- 1907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对此地进行发掘并出土了汉语和古突厥文的手稿[25]。其中部分藏品藏于新德里国立博物馆[26]。
而后中国考古学家逐渐出现在了此地的考古工作中。
- 1928年及1930年,黄文弼两次对此地进行调查。
- 1953年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考察组对吐峪沟石窟进行考察。
- 1961年,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委托对吐峪沟石窟进行调查和记录[25]。
- 201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合作对吐峪沟遗址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持续至今(2019年)[27]。
政府在遗迹保护上也有贡献:
- 1957年,吐峪沟石窟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 200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列入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25]。
- 2010年,筹划“丝路遗产——吐峪沟大遗址保护”[28]。
- 2015年,《吐峪沟石窟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完成[29]。
风险及自然灾害
參考文獻
- 陈凌; 李裕群; 李肖. . 考古. 2011, (07): 27–32+113+105–106.
- 陈凌; 李裕群; 李肖. . 考古. 2012, (01): 7–16+1+97–102.
- Ye-Na Tang; Xiao Li; Yi-Feng Yao; David Kay Ferguson; Cheng-Sen Li. . PLOSONE. 2014, 9 (1): e86363 [2022-04-12]. doi:10.1371/journal.pone.008636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11).
- . 丝绸之路世界遗产.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9).
- 王永强; 侯知军; 闫雪梅; 夏立栋; 田小红; 张杰; 艾涛; 胡兴军; 于建军. . 西域研究. 2018, (03): 126–136. doi:10.16363/j.cnki.xyyj.2018.03.015.
- 丁晓莲; 王龙. . 吐鲁番学研究. 2015, (02): 155–156+160. doi:10.14087/j.cnki.65-1268/k.2015.02.015.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4).
- 王瑟; 丁晓莲. . 光明日报 (09版). 2015-12-01 [2019-06-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0).
- 刘杰. . 新华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1).
- 符晓波. . 新华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10).
- 刘杰. . 新华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8).
- . 天山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6).
- 晁華山. . 神學論集. 1992, 94: 561–570.
- 贾应逸. . 佛学研究. 1995, (00): 240–249.
- 侯世新. . 龟兹学研究. 2012, (04): 263–271.
- 赵阳; 陈爱峰. . 敦煌研究. 2013, (06): :24–28+143.
- . 凤凰网·佛教.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09).
- 郭梦源; 苏玉敏; 秦大树 袁旔(编). . 2011:古丝绸之路:亚洲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3: 149-158 [2019-05-26]. doi:10.1142/978981455116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0).
- 佚名. . 国学. 2014, (03): 78–79.
- 陳凌. . 欧亚学刊. 2015, (02): 35–51+10–15.
- 张惠明. . 敦煌研究. 2010, (01): 92–97.
- 张惠明. . 中国美术报. 2016年4月25日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5).
- . 中国佛教协会.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6).
- 荣新江.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2 (04): 16–26.
- Chen Ling; Li Yuqun; Li Xiao. . Chinese Archaeology. 2012, (12): 21–27. doi:10.1515/char-2012-0003.
- 郑弌. . 人民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18).
- 毛咏; 江文耀. . 天山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6).
- 安士佳. . 天山网.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6).
- . 丝绸之路世界遗产. [2019-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1).
- 王亚红; 周双林. . 丝绸之路. 2016, (20): 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