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注
《文心雕龍講疏》是范文瀾對於《文心雕龍》的注本,於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書局所印行。在1929年,作者又將更名為《文心雕龍注》,簡稱范《注》,於1929年由北平文化學社所印行。及後,《文心雕龍注》在1936年由上海開明書店修訂,1958年又由王利器作修訂,成為最通行的版本。
| 文心雕龍講疏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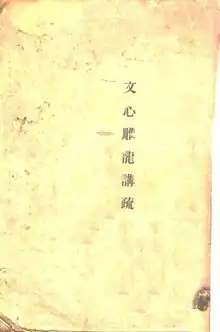 | |
| 作者 | 范文瀾 |
| 發行 | |
| 出版机构 | 新懋印書局 |
| 出版時間 | 1925年 |
| 出版地點 | 天津 |
此書在學界被高度重視,取代了《文心雕龍輯注》風行半世紀的位置,在出版之後成為了《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參考書。戶田浩曉認為,「此書不可否認是《文心雕龍》注釋史上有劃時代的作品」。[lower-alpha 1]:158王更生認為,此書為是學人「投石問路的憑藉」,問世「真如石破天驚,給我國學術界帶來相當的震撼」。[lower-alpha 2]:109
學界對於當中《文心雕龍注》也有所不滿意之處。在1952年,斯波六郎寫作了《文心雕龍范注補正》一文,當中以開明書店版對於范注中的典故引證、文本的校勘和語句解釋有所補正。[lower-alpha 3]:2。在1967年,張立齋創作了《文心雕龍注訂》一书,在書中他認為范文瀾所作之注不便於近代學子,因此重新將釋文有所發凡,而范文瀾所作之處不足者加以補正。[lower-alpha 4]王更生在1979年所作之《文心雕龍范注駁正》中認為范注「瑜中有瑕」,「可資取法的地方很多」,還沒有到檢跡殆遍的地步。[lower-alpha 3]:ii
創作動機
他創作《文心雕龍注》的動機主要有三個,第一是為了教學上的需要,其次是受了黃侃《札記》的啟發。范文瀾在1914年考入北大,在黃侃門下學習,1917年畢業,並在南開大學任教,其中之就包括了《文心雕龍》。按書中自序所言,他看到學生經常因為《文心雕龍》中的問題而前來請教,為了教學需要而寫成講疏。[1]:24
此外,范文瀾受學於黃侃的時候,雖然受其啟發,但是也發現當中的義理並不全面,希望補足《文心雕龍札記》(《札記》)不足之處。黃侃在《札記》中都指出《文心雕龍訓故》的記載並不全面,轉載而不著名出處,而范注本也同樣都指出了這個問題,可見他也受《札記》的影響。[1]:24
據林甘泉回憶,作者出書是為了掩護地下党的運動。新懋印書局是中國共產黨在天津的秘密印刷機構,由彭真所主持。當時書局需要公開出版一些書籍以掩護,於是便油印他的講義。為了不被南開大學增加麻煩,只是以「華北大學編輯員」的名稱出版。[2]:177-178
流變
此書在1925年以「文心雕龍講疏」之名由天津市新懋印書局所梓行,及後作者對此又多次修改。在1929年他修改了講疏的內容,並以《文心雕龍》注名稱出版,由北平文化學社出版《文心雕龍注》上冊、中冊,在1931年出版《文心雕龍注》下冊。1936年,上海開明書店又再從文化學社版作修改出版[lower-alpha 3]:1。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王利器又一次订正[3]。1960年,香港商務印書局重新校定之後又再出版。1970年,台北明倫出版社对于范注加以修订后出版。[lower-alpha 3]:1
1925年:天津新懋印書局版
在1923年,他創作的《文心雕龍講疏》(《講疏》)已經完稿,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書局出版,當時尚以《文心雕龍講疏》一名發行。全書約500多頁,約有近30萬字左右,不計算《文心雕龍》原文則有20萬字。書前有約一千字的自序,以及是梁啟超的序。在自序中,他除了說明自己的創作背景之外,也說明了《文心雕龍》的一些要義。《講疏》中注文分插在各篇的分段之下。[4]
1929年:北平文化學社版
1927年,范文瀾回到了北京,並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學校任教。北京作為當時的文化中心,為作者重新修訂帶來良好的條件。對比兩個版本,作者新補了條目375條,修改了條目721條,刪除了條目31條,當中只有223條的注解是沒有修改。因此,范文瀾對於《文心雕龍講疏》可以說是回爐重造。[2]:179-181
當時,作者和孫蜀丞、趙萬里、陳准等人交流之下,得到了《文心雕龍》很多的善本和最新的校勘資料。作者在寫作《講疏》的時候,曾表示「以未見此本(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為恨」。通過陳准,作者看到孫詒讓手錄的顧黃合校本,並以此校讎文本。此外,孫蜀丞所校的唐寫本、明抄本《太平御覽》、《太平御覽》[註 1]三種版本也為他的校正帶來了方便,而孫氏對於唐寫本的研究也被錄入了書內。趙萬里當時在《清華學報》上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校記》也被摘錄進去。但是正文主要摘錄的都是孫蜀丞的校語,趙萬里的校語只是佔少數。[5]:644-653
另外,作者也試圖消解初版中的講疏體色彩。例如在《原道》之中,作奢引綠了大量劉師培《論文集記》和黃侃《札記》中的內容,而在《注》中,作者改為引用了孫蜀丞的說法、《周易音义》、《说苑·反质篇》和《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等引文。又例如是《諸子》一節,作者本來在其中說明《諸子》中的思想應該如何在現實中致用,但是在修訂之中,作者刪去了主觀言辭,改為說明當中的出典。[5]:653-656
針對於過於倚重《文心雕龍札記》和《文心雕龍輯注》的問題,范氏盡可能淡化當中的影響。在《輯注》方面,以《書記》篇為例,作者引用了《輯注》23條,在修訂後只餘下一條。而且修訂當中,一些稍微變更者直接刪去「黃注引」等字句,直接引錄書籍原文以達到減化影響的作用。[5]:656-661
1929年,北平文化學社出版了《文心雕龍注》,兩者的體例大致相同,但是字數由《講疏》的20萬字,增加至40萬字[4]。一共分為三冊,上冊為原文,下中冊為注文。上中冊於1929年出版,下冊於1931年出版[lower-alpha 3]:1。和講疏對比,范注中例言中隻字沒有提《講疏》,也沒有提及《札記》,只是在書中略為和陳漢章並列而提。而梁啟超為范文瀾所作的序都沒有錄入范注之中。王運熙表示,這種情況「似覺奇怪」。[4][1]:24-25有學者認為,這個現象是范文瀾不希望《講疏》為人所知所致的。范文瀾雖然自稱自己是因為教學需要寫成《講疏》,但是范氏同門(刘赜、骆鸿凯)都和他同校,而他們所擬的教材以經史子書為主,沒有包括《文心雕龍》。而駱鴻凱在1922年探望過黃侃,以致黃侃可能在《文心雕龍講疏》發表前己經知道范文瀾打算出書,但是黃侃要求學生沉潜用功而不急于出书,也要求自己不在50歲前出書。再者黃侃在對於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多有讥评,而假如《講疏》注明自己是出於師教的話,就可能使黄侃难堪。[6]
1936年:上海開明書店版
作者將《文心雕龍注》重新修訂之後,交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並分作七冊綫裝本。相比起文化學社版,開明書店版在凡例之後增補了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黃叔琳文心雕龍校勘記》的例言和校勘書目,並在正文中夾校大量采用了鈴木的校語。[7]此版本中注文又重新放回正文各篇下。[4]開明書店又於1947年12月再版此本。[8]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
據王利器的回憶,最初范文瀾並不同意再刊此作,認為是「少作」。他表示,「自己作為責任編輯,一定會盡力將工作做好」。在過程中,他訂正補充了約五百條注文,范氏看到了之後,表示全部同意,並提議在著者上署上他的名字。王利器表示並不同意,認為這只是責任編輯應該做的。而即使在他自己所作的《文心雕龍校證》之中,他也沒有使用自己為范文瀾所訂補的注文。[8]:101-102王利器對於范注修訂主要可以分為增補、訂正、補充、厘正等四項。[9]
1967年:張立齋的《文心雕龍注訂》
在台灣,張立齋有見於歷史《文心雕龍》注本的谬误甚多,希望「以正诸本之讹失,与补其所未備」,在范注的基礎上作補正。他於是寫作《文心雕龍注訂》一書,由正中書局於1967年出版。台灣各大學中文系大多都以版本作為講授的課本。[10]
整篇的文字分段完全依照范注。在全書中,明指范注出錯之處有至少有112處,並指他本至少8處錯處。張立齋也可盡可能對於范注未注解的位置給予注解,例如在《原道》篇就補充了注解至少18條。在修訂過程中,有些注解直接抄錄在其《注訂》,有些就位置則打亂以引用之。[10][lower-alpha 4]
評價與補正
對《講疏》的評價
在《文心雕龍講疏》出版之後,范文瀾將他的書寄到了各大圖書館,如清華大學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等都收到他的作品,魯迅也有收到了他的著作。[6]:50
在出版半個月之後,《南開月刊》出版了一篇帶有廣告性質的短文,作者署名壽昀。他指,「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是敢负责任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並書後以“虔诚的请你们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作結,大有廣告意味。[6]:49-50
署名章用[註 2]的的《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提要》先肯定了范文瀾「傳習師訓,廣為講疏」後,指出了范文瀾雖然以「講疏」為名,但是卻「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指作者對於《文心雕龍》的劃分方式有誤,而且沒有以章、句作單位了解釋全文,並只是按着《札記》的方式創作,缺乏自己的創新。他又指,作者直接抄錄一些常見文章,實無必要,如《辨骚》篇抄录了屈原《离骚》,《明诗》篇抄录了钟嵘《诗品》等等。[6]:50-51
署名李笠的《读〈文心雕龙讲疏〉》對於他的體例作出了一些批評。他認為主要需要增補的有八點:包括成書考證、劉勰年譜、刘勰遗文、旁证、引书出处、注释、校勘、补辑。而且,此書的正文和注疏之間的分別,以及是注疏本身也有整理的必要。[3]:35
對於文化學社本的補正
在開明書店版發表次年後,楊明照發表了《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一文,舉出文化學社本中范注中有三十七條不當,而且有14條將黃叔琳的評語誤當是紀昀的評語。當中,14條錯誤中有10條已經在開明本修訂中被改正,其他至王利器修訂的時候才被修正。[11]
對開明本的補正
楊明照在1938年又撰寫了《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文,認為「黄注探囊揭箧, 几一一鹤声」,指范氏抄襲過多。但是楊明照本人也可能認為當中的批點有所不當,因此沒有收入论文集《学不已斋杂著》中。[12]
斯波六郎在1952年發表了《文心雕龍范注補正》,當中以開明書店版對於范注中的典故引證、文本的校勘和語句解釋有所補正。[lower-alpha 3]:2當中,「補」有359條,出典補遺有285條。「正」有84條。王利器在修訂的時候也有參考斯波六郎的舉正。[13]但是,他的舉正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他對於非常簡單的字詞也出典,如「吹毛取瑕」(《奏啟》)、「文史彬彬」(《才略》)等,缺乏相應的出典價值。再者有一些指正是范文瀾已經征引了的,但是斯波六郎對此再重復征引。[14]
王更生的《文心雕龍范注駁正》
台北華正書局在1979年出版了王更生的《文心雕龍范注駁正》。在書中,王更生按1970年台北明倫出版社的增訂本,認為范文瀾所作的注主要有「采輯未備」、「體例不當」、「立說乖謬」、「校勘欠精」、「注解錯訛」、「出處不明」等六項問題。
「采輯未備」方面,王更生認為「知人必先論世」,指除了《梁書》、《南史》之外,尚有很多史料和《文心雕龍》本身可以作為考見他家庭大事、著書立說的體例,和同時代人物的關係,但是資料足夠的情況下,卻依然沒有為劉勰編著年譜。他又指,范書末所引《梁書·劉勰傳》中沒有收錄《序志》原文,認為魏徵所見的《文心雕龍》和今日所見的《文心雕龍》版本有所不同,具有收錄價值[lower-alpha 3]:8-10。在版本方面,范文瀾沒有在書前列出其考據所依版本,而這使讀者沒有辦法理解《文心雕龍》各版本流變[lower-alpha 3]:10-12。而他又指出,范沒有收錄前人的序蹳、評點、著錄,而他們提供了《文心雕龍》內涵的不同角度[lower-alpha 3]:13-15。此外,他也批評沒有收錄劉勰的其他遺著,沒有起到相互發明的作用[lower-alpha 3]:15-16。
「體例不當」方面,他指作者收錄了日本學者鈴本虎雄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的例言和校勘書目,但是鈴本虎雄一書出版以1928年,在開明書店版的25年之後,難免讓讀者產生奇怪的感覺,收錄日本作者的書目與當時國家的思想出現了偏差的傾向,不合著書的體例[lower-alpha 3]:16-17。他又指范氏有時候解釋《文心雕龍》各篇篇旨,有時候又沒有解釋,沒有明確規例,使讀者沒有辦法理解當中的規例。校勘有時夾於正文,有時候於附注,有時候只校不注,有時候別目單行。稱謂方面,有時候單純以某某曰,某某,而沒有說明具體出處,有些就算有說明引用書目,但是沒有說明卷次。[lower-alpha 3]:18-24
「立說乖謬」方面,他指作者的圖表組識沒有根據,指他自行創作,不依原文,已經到了「不可原諒」的地步。[lower-alpha 3]:25-29而且《序志》已經說明《辨騷》是文原論,但是范氏分於文體論而非文原論划分結構。[lower-alpha 3]:29-33他又指作者雖然有對於創作論有自己的看法,並以圖表說明了創作論的體系,但是他為了「剖情析采」的對稱性,因此圖表有所不妥。[lower-alpha 3]:33-37
王更生又詳細指出范注中有多處誤校、失校之處。他又指出范文瀾沒有弄明劉勰行文詞例、字例以及造語之例,引致注釋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某些地方出處不當,不明,或者征引不足。[lower-alpha 3]
李平認為王更生批評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是有着時代背景,他認為《文心雕龍范注駁正》是成書於1970年代,當時台海相隔,因此假如措辭、人名、引說不慎,「極有可能被摜上思想偏左,與敵同路的紅帽子」,而他所指的「采輯不備、體例不當、立說乖謬」的問題只是著述特點的不同,習慣相異,觀點不同,只是強人所難,而且他的讚詞也未必合乎實情,例如他指范注「引文豐富」,但是范文瀾對自己的《文心雕龍講疏》或者是《文心雕龍注》從來也是自視不高。他在五十年代再版的時候也再三推辭,認為是「少作」,出現了不少問題,甚至認為是自己「以追踪乾嘉老輩」......「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標時期的舊我之舊作」。而關於沒有年表的問題,他認為劉勰的身世、本傳、史料極為簡缺的情況下,范文瀾依然在當中推算了劉勰的大約生平大事,在身世上有研究之功,而王更生也在《文心雕龍研究》中認為:「范氏注《文心雕龍》,於《序志》篇曾根據劉氏(劉毓崧)書後,賡考產和一生行事,行文雖半出於臆測,而衡情度理,亦以意逆志之作。近人雖然大力搜討,欲更新舊說,但限於材料,仍不越范注的範圍。」,李平認為王更生兩書所言「簡直天壞之別,完全判為兩人」。而且王更生自己在《文心雕龍研究》中也沒有在《梁書·劉勰傳》中收錄《序志》原文,李平認為這可見他是「具有違背學術良心的政治獻書的色彩」。[15]
參考
論文
- 戚良德; 李婧. .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 (05): 23-29.
- 李平. . 中國詩學研究. 2019, (02): 177-190.
- 李平. .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 42 (12): 35-49.
- 王運熙. . 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 5 (2): 72-73.
- 李平. .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2019, (02): 644-661.
- 張海明. .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 35 (04): 45-71+212.
- 李平. . 中國詩學研究. 2020, (01): 30-46.
- 李平. . 學術界. 2003, (04): 101-104.
- 李平. . 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 05 (03): 59-64.
- 李平. . 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34 (03): 7-15.
- 李平. . 中國典籍與文化. 2019, (03): 42-49.
- 李平. . 中國詩學研究. 2017, (02): 95-114.
- 李平; 黃誠禎. . 文化與詩學. 2019, (02): 212-223.
- 李平. . 北方論叢. 2019, (01): 32-37.
- 李平. .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 (编). .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97-127. 2017.
書目
- 张少康; 汪春泓; 陳允鋒; 陶禮天.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2022-05-06]. ISBN 7-301-04982-X. OCLC 4892929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31).
- 張文勛. . 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1. ISBN 7810682083.
- 王更生. . 台北: 華正書局. 1979. OCLC 645725995.
- 黃端陽. .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12. ISBN 9789863140535.
注腳
- 范文瀾「例言」中原文如此。
- 關於章用是何人,一說是章士釗,一說是駱鴻凱。